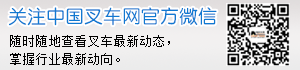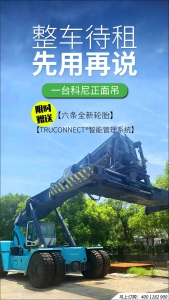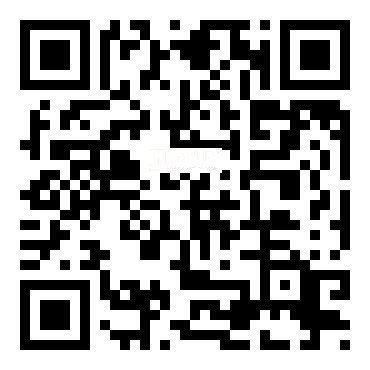现实却令人失望。在当时主流的思想体系里,工人是工厂的主人,但是“主人”一点也不爱工厂。机械厂有很多二手设备,“只要机器一出毛病停产,工人们帽子一甩,高兴得嗷嗷嗷嗷大叫,欢天喜地就下班回家了。”袁金华说。
这让梁稳根和袁金华等人备感失落,“国家还这么穷,这样子怎么能富强”,梁稳根、袁金华说他们那一代人天然有种家国情怀。袁金华读初中时,他哥哥有位同学是教育局长的儿子,家里订了份《参考消息》,谈起当时的国际局势头头是道,袁金华觉得这个人“神奇透了”。2012年12月12日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,提到当年的胡耀邦等人,54岁的袁金华忍不住红了好几次眼圈。
他们对工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。厂长王福全对这几个“不安分”的年轻人颇为赏识,工作一年多后,梁稳根就成为了机械厂的体改委副主任,属于副处级干部,唐修国等人同样也得到了被提拔的承诺。随后,梁提出能否承包一个车间,推行改革自负盈亏,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准许。
那时候,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是步鑫生和马胜利。熟读西方管理学著作的梁稳根觉得,步和马那一套非常粗糙。梁等人认为自己不比他们差,他们决心成为中国一流的理论家和一流的实践家。
按照梁稳根最初的想法,他们要了解十个行业、调研十个项目、存够10万元启动资金之后,才辞职下海。不过几个人准备辞职的风声已经传遍全厂,而他们的“出位”又被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干部视为爱出风头的反面典型,辞职计划不得不提前落实,而风靡中国的下海大潮还要等到7年之后的1992年才到来。
梁把此次辞职下海定义为一场社会试验,“给后来者提供样本”。这种将个人选择赋予历史使命的光荣感和悲壮感,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失去了铁饭碗的恐惧。
接下来的离职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冒险。
梁和几个同事提出离职后,工厂方面扣押了他们的档案和户口本——当时要领到买口粮的粮票必须拿着户口本,没有户口本意味着他们连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。
梁本人并非莽撞之徒,他知道该找一位在涟源县有话语权的人寻求保护。1985年10月,他找到了县委书记阳花萼。2012年已经78岁的阳花萼只读过三年书,但是思想相当开放,自学上网。阳当年也属于改革派人物——为了鼓励县里的经济发展,他组织了一百多名县里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的“落后分子”,让他们佩戴大红花在县城里游行了一大圈。
开明的阳花萼答应提供保护,免得他们被机械厂抓回去。
阳花萼还承诺,“干不成到县里当干部去”。但是梁稳根等人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,“如果失败了就去边疆支教度过一生”。
梁的父亲却对这场前途未卜的冒险出离愤怒,拿着扁担想把梁稳根赶回去,当初跳出农门时,梁曾是村民鼓励儿孙的榜样。
其他三人也向家人隐瞒了这一切。袁金华的母亲写给袁的家信寄到厂里,却以“查无此人”为由被退了回去。袁母以为儿子遭遇不测,从贵州一路哭着坐火车赶到涟源。
“压力很大,不敢跟家人说,以前的同学也都不联系了。”袁金华说,同学有的已经当了副县级干部,他自己却为吃饭发愁。
经过贩羊等一系列失败后,他们在1986年成立了焊接材料厂,当时乡镇企业的标准称谓必须挂上所在乡镇的名字,为了使企业名字听起来更有底气一点,他们找人去掉了“乡”字,“叫涟源县茅塘焊接材料厂,这样的话人家可能以为我们是县级企业。”袁金华回忆说。
在
三一的历史上,这被认为是第一次创业。第二次创业是1994年的“双进战略”,进入工程机械领域,总部迁往长沙。第三次创业则是国际化。
“没想到啊没想到”。2012年12月23日,在三一集团位于娄底的生产基地办公室里,阳花萼连声说,他压根想不到当年那几个有些莽撞的年轻人“能干这么大”。
阳花萼把有关三一集团的所有新闻都放到了电脑的收藏夹里,他能随口说出三一最近几年的销售额,还推测三一起诉奥巴马赢面很小。不过,他话锋一转说,“这几个人啊,还是那么胆大,告奥巴马长志气。”
办公室外是喧嚣的生产基地,笨重硕大的银白色金属油缸,正被机器手轻巧地搬移到下一道工序处,这是混凝土机械的关键部件之一。如今,三一集团的混凝土泵车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%以上,连续多年产销量居全球第一。三一集团也成为中国最大、全球第六的工程机械制造商,并成为造富工厂。2011年,梁稳根先后登上胡润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之顶,首次成为中国首富,三一其他多位高管也入围榜单。
老大哥
值得一提的是,从1986年创业开始,四位创始人就从未分开过,这在中国企业界非常罕见——在逐渐做大的蛋糕中,他们如何保持了利益的平衡?
梁在创始团队之中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。唐修国、袁金华等人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都不掩饰对梁超出兄弟情谊的敬仰。
第一次分蛋糕,是在“双进战略”实施之后。1994年,梁稳根召集兄弟开会,明晰两个公司的产权,当时,是向文波刚刚加入三一集团的第三年。梁稳根提出的方案是,涟源材料厂的股权,梁、唐各21%,毛、袁各20%,其他高管分享剩下的18%。当时,主业为工程机械行业的长沙三一还处于亏损状态,梁稳根占50%出头一点,唐修国9%、袁金华、毛中吾、向文波分别占8%,随后梁还把一些股权分给了后来的高管。“当时涟源材料厂是赚钱的,梁总占50%都不为过。他不计较涟源厂的股份,长沙这块的股份就更没人计较了。”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回忆道。